文|互联网指北
提到“元宇宙”,大多数人会马上联想到“未来”。如今,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元宇宙”创业项目白皮书,他们垂直于社交、游戏、文创、Saas领域,带着对传统产业模式的“看衰”,试图提出具有“迭代意义”的解决方案。
老玩家也纷纷向元宇宙伸出触角,华米OV们沉浸于为元宇宙提供“物理基础”,拥有足够存量的腾讯、百度、字节跳动们的重心更倾向于“玩法”,TMELAND、希壤、虚拟人被实验性地推向前台。
可“元宇宙”真的能够带给我们那些预期中的改变吗?这个问题似乎仍然萦绕在很多人的脑海中。看衰者们认为:元宇宙只是一个技术概念,本质上指的是人类连接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人们能够通过这套新的衔接方式创造出来什么新东西,其实取决于“人类能够掌握的智能水平”——因此相比于“炒作元宇宙”,还是应该更关注停留在现实宇宙里,能够创造实际生产力的“硬科技”。
可能元宇宙最坚定的支持者们也很难进行有力的反驳。因为即使元宇宙真的有预期当中的“实际价值”,从技术诞生到商业再到民用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大多数人缺乏对元宇宙的实际感知”将是一种常态。在经济学语言里,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长时间不匹配,发展动力就会成为一个必然的问题。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反驳。早在2007年,就有一群艺术家通过“元宇宙”的形式,兑现过他们心目中的创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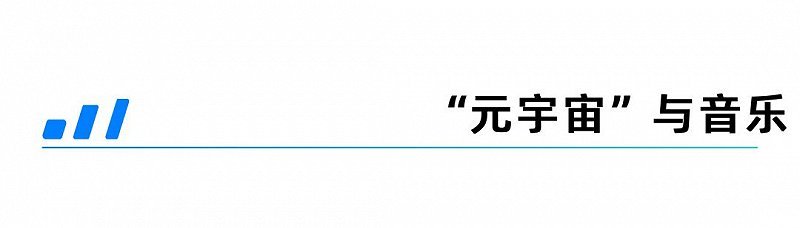
“元宇宙”能够在音乐产业得到大规模的应用,很容易被理解为资本市场基于“传播”的考虑。毕竟作为标准的娱乐消费,“音乐”能够给新技术的推广提供一揽子的便利条件,包括且不限于“陌生概念的包装”“使用场景的潜移默化”“具象使用价值”等等。
但对于音乐从业者来说,“元宇宙”也确实能够在生产力层面带来非常实在的提升,比如人们可以通过软件的模拟,低成本地解决设备问题;在编曲和表演阶段则可以提供一个必要的空间,让身处不同地区的人也能得到进行协作的机会。
只是这个愿景对“基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音乐协作”需要足够丰富且及时的视觉线索(比如肢体动作、面部表情、手势)和听觉线索来产生“配合质量”,提供服务的元宇宙产品必须想办法克服网络延迟、低带宽等客观因素带来的影响——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音乐元宇宙”产品一定会更多面向于C端,在观看、交易、收藏等环节上进行赋能。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难点,“临场感”。“临场感”指的是身处同一空间内的创作者,可以通过彼此的接触交流可以预判对方的下一步动作。
在学界,“临场感”被认为是音乐协作过程中的核心元素,失去“临场感”可能会直接影响参与者们的创造力,接着进一步降低参与者们在协作时的心情。
所以考虑到“创作”本质上是一个相当依赖灵光乍现的感性过程,“元宇宙”如果想成为音乐产业的生产工具,就不能仅仅只还原参与者的声音和长相,更需要对参与者的全身进行具象化还原。
再加上众所周知的一个常识是:大批量的图像处理任务,除了将严重消耗源站服务器的存储和计算能力,也能大口大口地吃到CPU和GPU的性能——这让早期的“元宇宙产品”非常容易陷入自我矛盾里:本来是寻求灵活便捷,但却在入门阶段设置了高耸的门槛,还带来了很多新麻烦,像张艺兴那样边走路边写歌的名场面肯定是不会有了,容易重死或者烫死。
值得一提的是,可能是因为“做难而有趣的生意”是全世界创业者们的普遍共识,“如何帮助音乐人完成云协作”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技术领域,被称为网络音乐表演(全称Networked Music Performance,缩写为NMP),包括乐器模拟、声场还原、声音识别等等。
据说远程会议产品就在NMP成型过程中吃到了大量的红利,有相当一批艺术家看重了会议系统的低延迟和网络同步。

(一群音乐人用zoom来实现元宇宙音乐协作)
当然还是老问题,前置摄像头并不能完全解决“视觉交流”的事,“元宇宙”对音乐创作的改变仍然是一个理论预期。

对于缺乏艺术细胞的人来说,阿凡达元宇宙管弦乐团(The Avatar Orchestra Metaverse,简称AOM)的作品观感实在是有些一言难尽。尤其是戴上耳机进行沉浸式欣赏的时候,持续的高频背景音+难以预判的动画展开+粗糙的建模+暗沉的色调,很容易产生颇具宗教仪式色彩的“创世感”。
但对于元宇宙行业发展史,AOM闪耀着先锋意义。
时间回到2007年,虽然泛“元宇宙”概念的产品已经萌芽,但互联网世界对它们的态度并不友好,因为那时的人们普遍默认的事实是“3D虚拟空间”是一项应用于“游戏”技术,相当一部分媒体粗暴将“可以创造虚拟形象、帮助人们实现线上互动”的产品定义为类似魔兽世界这样的MMOPRG(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另一部媒体提出了“异议”,认为它是类似于“模拟人生”“模拟城市”式的经营类游戏……
这样的刻板认知直观地影响着资本市场对于他们的判断。投资人们带着“游戏”的视角进行了体验,发现这些产品很无聊,最高频的使用场景无外乎穿搭和聊天。除此而外,还触及到了法律的边缘地带——一部分“元宇宙产品”对于现实世界的模拟,延伸到了“性”的部分(虽然只是动作上的模拟),德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曾经因此进行过“元宇宙扫黄”,理由是有用户在里面还原“强制性行为”,更有甚者还“模拟儿童的形象”来龌龌龊龊。
NBC就用“如果不是游戏,那它到底算什么”作为标题报道过这个争议赛道,“元宇宙扫黄”的当事产品“第二人生(Seconl Life)”开发团队Linden Lab在其中正面回应了它们的定义争议:“我们既不去制造任何用户之间的冲突,也没有设置任何既定目标,这是一种完全开放式的使用体验,请叫它‘3D在线虚拟世界’。”
可想而知,这句话一点用都没有,被商业文明反复毒打过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共同认知是“论迹不论心,论心皆PR”。
带着一片混沌,AOM和“第二人生”一拍即合。
“第二人生”这一代元宇宙产品虽然外观粗糙,对接的场景远不如现在丰富,但就像癞蛤蟆找青蛙——长得丑玩得花,它们往往很安心于成为一个开放的底层技术接口,鼓励用户去创造、建造,自己定义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而AOM虽然自我定位为一个使用虚拟乐器在虚拟世界中进行音乐排练和演出的乐团,但大多数人并不是职业的音乐人,成员拥有学科背景相当丰富,包括建筑、视觉艺术、声音艺术,更像是一个“借用音乐来进行思想试验”的“艺术家团体”,在“不务正业”这件事上展现出了极强的专注:除了进行“音乐合作”,他们非常热衷于搭建表演时需要用到的景观、建筑、服装、道具等等。
然后就像历史书里告诉我们的那样,当改变欲望足够强的群体,进入传统色彩足够薄弱的环境,生产力解放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2007年3月,AOM在第二人生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公演,作品是13th Vicky's Mosquitos。瑞典人Miulew Takahe担任编导,演出成员遍布整个西欧,包括身在德国的Maximilian Nakamura、身在荷兰的Frans Peterman、身在法国的Hars Hefferman和身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乐队Pomodoro Bolzano。
其中Pomodoro Bolzano乐队成员Bingo Onomatopeia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里世界(inworld,指在“第二人生”的世界里)乐器aviophones。按照官方博客的说法,aviophones“不仅能发出声音,还能找到声音”。
这样的描述多少有些抽象,结合AOM成员Wirxl Flimflam的博客所描写的演出经历,aviophones可能更适合描述为“声音样本模拟器”,能够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全看它之前的采样——有可能模仿吉他、二胡、唢呐演奏出来的“哆来咪”,也可能取材菜市场或者洗澡堂。在2007年5月,也就是初舞台的两个月后,AOM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发现声音”的创作活动来进一步诠释创作理念:
他们在德国雷根堡的Haidplatz广场设置了一个实体版aviophones(用集装箱卡车改造),录制了一些“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经常能听见”““无处不在,以至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声音小样,然后上传到“第二人生”。身处里世界的乐团成员们通过行走、跑动等方式触发aviophones,人越多越能产生交响乐效果。
与此之类的还有Onomatophone,AOM将其描述为一款真三维乐器,原理是在虚拟空间里设置6个用于发声的“小球”,人们通过不断地穿梭其间、改变接触面积来创造不同的声响。
一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成员尝试按照这种思路把自己变成一个乐器,即设计一套动作捕捉算法,让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发出声音。也可以用这种思路来联动演出环境里的景观和建筑,景观和建筑的形状和颜色会跟着声音(动作)的变化而改变。
合奏阶段强调的是“即兴创作”,不一定要按照“乐谱”进行演奏,更多时候鼓励成员们进行“涂鸦”。“涂鸦”的概念借鉴于英国即兴演奏家约翰·史蒂文斯,他经常使用这个词来指代“不受大脑控制的快节奏即兴创作”。约翰·史蒂文斯去世之后,AOM还为其在2010年10月举办过一次纪念专场,主题是“声音艺术的新冒险”。
说到这里,其实也就不难理解开头那段AOM的演出视频,整体效果为什么会那么魔性,因为他们所做的就是彻彻底底的“实验音乐”,哲学式的表达远远多于抒情式的表达,而粗糙的“第二人生”又“恰巧”能还原哲学家们内心世界里不断地矛盾与质疑。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发展到后期已经成为音乐节、电影节、艺术周的常客,AOM也一直没有尝试商业化。更多时候他们对一些迷之领域表现出了迷之热情,例如心灵感应。2020年10月,他们就和心灵感应团队Breathing PwRHm合作,进行了一场名为“呼吸在赛博空间”的直播活动,AOM演示如何在虚拟空间中创造聆听、感知、共鸣,Breathing PwRHm致力于探索通过赛博世界影响“身心灵”。

其实AOM并没有解决前文提到的那个问题:元宇宙不是一个能够投入到量产阶段的生产力工具,对于使用者和使用场景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以至于整个产业将长期停留在“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严重脱节”的情况。
关于实际操作过程,AOM给出过一个有些模糊的官方解答,大体意思是在表演时需要设置多个显示屏,一个用来显示客户端界面(用来让表演者们看到具体的呈现效果,作用有些类似于舞台表演时用到的“耳返”),另一些用来呈现一些可视化的数据,AOM成员通过这些数据来控制声音、角色的动作和视觉效果。
AOM成员Norman Lowrey拍摄的演出视频把整个过程展现得更具体一些:Norman Lowrey在一个布置了大量设备的舞台上进行表演,他的两个助手(也有可能是伙伴?)盯着好几台不断产生数据的电脑进行实时操作,舞台上同时也放置着“第二人生”的具体画面。
但AOM教会了我们如何与“下个时代”相处。
Norman Lowrey是很典型的“AOM”。他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这样介绍自己:面具制作人/作曲家/表演/声音/视频艺术家,德鲁大学的音乐荣誉教授,拥有伊士曼音乐学院授予的博士学位。
他曾经发起过一个名为River Sounding的项目:邀请人们一起聚集在特拉华河沿岸,静静地聆听河流的声音,然后再创造出作品向人们讲述“你聆听到了什么”。这些作品包括且不限于面具、陶瓷、木雕、皮革、虚拟面具,而他比较擅长的是“音乐面具”——用芦苇、齿轮、电子管等材料制作成能够佩戴在脸上的发声装置。
AOM成员人均如此,也大概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用“阿凡达”来定名自己——不仅仅是因为“阿凡达”讲的就是人类通过脑机接口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阿凡达”告诉人们,进入另一个世界并不意味着“从零开始”,而是现实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互通有无”。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特雷门琴”,一款诞生于电气革命时代的乐器,发明者是俄国电子工程师李昂·特雷门。他根据“人体本质上是个导体”这个原理,巧妙地让电波变成了可控的发声装置,极大地开拓了人类所掌握的音域,以至于在四五十年代助推好莱坞掀起了“原声配乐”的革新热潮;但李昂·特雷门并没有停留在音乐市场上,他更重要的成就是奠基了射频识别技术,然后发明了运动侦测设备。
带着乐观的心态去展望,可能我们距离元宇宙时代,就差一个“特雷门琴”;尤其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相比起成为希壤、啫喱的早期用户,学着成为“阿凡达”可能才是真正意义下的时代入场券。
老朋友洪咸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Music Making in Metaverse,Music and Metaverse
Avatar Orchestra Metaverse plays In Whirled (Trance),Norman Lowrey